摘要:
谢帆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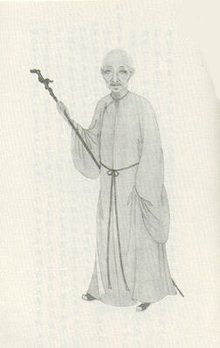
魏禧
清康熙四年(1665)四月,宁都魏禧拜会南丰程山。
程山,是清初名儒、程山七子之首谢文洊讲学的地方。那时战火初熄,锦绣江山又焕发出新的生机,人文荟萃的江西渐渐形成了宁都易堂、南丰程山、星子髻山三个教育中心,统称江右三山。三山政治立场一致、学术观点相近,都反对空谈心性、强调道德实践、倡导经世致用,但论及如何经世却还有不同见解。谢文洊一直想来一次会讲,把各自的观点讲清楚,相互砥砺以求增益。恰逢髻山七隐之首宋之盛前来拜访,谢文洊便盛邀易堂九子首领魏禧来南丰。
如切如磋,自有电石火花。
果然,会讲一开始,便有浓浓的火药味。谢文洊本来先为会讲定了题目、规矩,魏禧到来之后,立即提出修改。谢文洊、宋之盛心想,改就改吧,放马过来就是。
当时人们评价魏禧,说他如同新磨的宝剑,光芒逼人锋锷刺手。但谢文洊、宋之盛,又岂是浪得虚名之辈?
他们都有光明俊伟的人格,作为肝胆相照的诤友,词锋总是锐利,不屑于掩饰自己以取悦他人,哪怕这“他人”是益友、是良师。春天的程山,花影扶疏,“三山”你来我往唇枪舌剑,激烈的论辩一直持续了10天,相互间谁也没有说服谁,但大家都觉得怀抱大开、胸臆尽抒,快哉快哉!
魏禧后来评价说:这一次会讲,“直比鹅湖之会”。
真比得上鹅湖之会?
他们到底争论些什么呢?
宋之盛评点谢文洊的文集时说得很分明:
叔子欲经世而正人心,先生欲正人心而经世。
叔子便是魏禧,先生是指谢文洊,宋之盛说,魏禧和谢文洊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?魏禧认为在社会治理的行动中才能完善自我,而谢文洊相反,认为要完善自我才能更好地实行社会治理。
这是不是“鸡生蛋、蛋生鸡”啊?
学问家就争论这些东西吗?
是的,思想史上充斥着这类问题,譬如彭士望提出来类比的鹅湖之会。
鹅湖之会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朱熹、陆九渊。南宋淳熙二年(1175),也是春天,朱熹来到江西铅山,在鹅湖寺与陆九渊等人论辩了三天,焦点是为学之道应该“尊德性”还是“道问学”。
朱熹主张“道问学”,通过广博的问学致知,通达圣人之学,才能使人心与天理合一。陆九渊却觉得这法子太过零碎,应该“尊德性”,“宇宙便是吾心、吾心即是宇宙”,“六经皆我注脚”,如果不能发明本心,只是向外求索,那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。
陆九渊不单争辩,还要写诗,朱熹的诗名远在他之上,他却不管,似乎有意要在对手最强的地方出拳,他在诗中说:“易简功夫终久大,支离事业竟浮沉”,明显语含讥讽。朱熹最后拂袖而去,四年后又路过铅山,陆九渊专程来见,虽说两人友好如初,朱熹还是耿耿于怀,这时和诗一首,通篇说学问、说情谊,却仍不忘沾沾自喜于陆九渊所讥讽的“支离事业”:“旧学商量加邃密,新知培养转深沉。只愁说到无言处,不信人间有古今。”言外之意,是觉得自己通过博览穷理,直上圣人阶梯,可以与古人比肩了,而你陆先生的“易简功夫”“久大”了没有,恐怕还是未知数吧?
不知道这一回合陆九渊是怎么应对的,400多年后,清初黄宗羲却对两人的争论表示不解,他说:陆九渊推崇发明本心,其实也很努力钻研经典;朱熹强调问学格物,也时时观照内心,两家其实是一家啊,怎么弄成了冰炭水火?
黄宗羲,堂堂大儒,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,也不懂朱陆异同、认为这争论无关紧要吗?
不是的。
无论是朱熹还是陆九渊,无论是“支离事业”还是“易简功夫”,不过是为学的门径罢了。而黄宗羲处于明清易代之际,天崩地裂海立山飞,眼睁睁看着那么精深的学问、那么纯粹的德行,最终都束手无策,并不能挽狂澜于既倒。黄宗羲其实就是说,朱熹啊,陆九渊啊,左说右说的,不是闭目养性就是闭门读书,有什么用呢?
平时袖手谈心性,临难一死报君王。在黄宗羲看来,这教训无比惨痛。春风浩荡,黄宗羲眼见的都是鲜血,不是朱熹优游泗水,身边安排着万紫千红。
那么,要不要为学、要不要追求圣贤之道?如果要,又该如何去追求?
黄宗羲的时代,思想家们的回答就四个字:经世致用。
不是格物致知,目的不是致知,不管对这个“知”加上怎样的修饰词,统统都不是目的。为学的目的只在于“致用”,只在于“用”。
他们超越了鹅湖之会一般的认识论之争,而聚焦于改变世界的方法论。就魏禧等人而言,无论“欲经世而正心”还是“欲正心而经世”,都意识到了实践对于观念的作用,面对漆黑一团的世界,他们都明白人们应该有所行动——这就是圣人之道,是天理。
而他们之间尚有争论:“致用”,该如何“致”呢?
“三山”的分歧在于“仁”与“术”的关系。
谢文洊和宋之盛重“仁”,认为心中充满了“仁”,那么言行自然就能符合天地之理。魏禧不以为然,他认为脱离了日常行为,“仁”往往就虚无缥缈,“术”才是实实在在的,只有勇于任事、着眼于事业的成败,这样“仁”才能涵养于胸中。他在《日录》里写道:我过去也是把“仁”摆在“术”的前面,认为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就是这样,后来发现这“仁”字有许多说法,并没有确定的标准,久而久之便生出许多虚伪欺诈,所以我只好先把“仁”字放在一边,紧紧抠住“术”字,做每件事都兢兢业业,这样反而能在日常行为中发现“仁”的苗头。
这就是魏禧的“致”:着眼于日常,以事功为标准,“仁”就在其中了。
后来,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,在延安,简陋的窑洞里,伟大的思想如同朝日喷薄而出,毛泽东写道:“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。”
魏禧他们自然达不到这个高度。
但是,从鹅湖之会到程山会讲,人们能看见中国哲学正向这个高度缓慢而坚定地攀登。
多么令人动容的攀登!
魏禧、谢文洊和宋之盛,他们都是君子,言行一致,都按照自己的理论去生活:谢文洊广收弟子,砥砺德行,最终在《清史稿儒林传》中占有一席之地;而魏禧,则高居《清史稿文苑传》第一位,他本人虽然不科举不做官,却倡导“有用之学”,教导弟子们掌握治理国家的本领,更积极地融入世俗的生活。甚至在允许吟风弄月的诗文小道中,魏禧也坚决拒绝了无病呻吟,字字句句关心民瘼、颂扬英烈、探讨历代治乱得失,并在文学史上第一个提出“文以载道”不足以概括文学的功用,文学不应该止步于间接作用,而应该像粮食和布匹那样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。
在韩愈提出“文以载道”之后,魏禧提出并践行“文以经世”,中间是漫长的千年!
但魏禧并不寂寞,他辞世200多年后,一位哲人把文章当作匕首、投枪,并立下遗嘱: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。
他更收获了一句不平常的赞语——青年毛泽东在他的《讲堂录》中,端端正正地写着:“魏禧破产不为家,有似张良为人。”
《讲堂录》是毛泽东1913年的课堂笔记,内容涉及先秦哲学、楚辞、汉赋、汉书、唐宋古文、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思想家与文学家等,包含大量的毛泽东认为值得谨记并践行的修身格言,从中能强烈感受到青年毛泽东丰富的精神世界、崇高的理想人格和努力追寻的人生境界,是研究毛泽东成长、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资料。该书涉及魏禧及其兄长魏际瑞的竟有四条之多,其中三条是摘录和化用,最后一条便是上文所引用的,直接评价魏禧的“为人”。自然,现在已难以辨别,这一句是出自老师之口,还是毛泽东自己的心得,但毫无疑问,毛泽东认为这足以概括魏禧的德行功业。
这样高的评价,在整本《讲堂录》中并不多见。
在青年毛泽东眼中,魏禧最重要的身份并不是文学家、思想家,而是张良那样的行动家、那样的志士仁人。和张良一样,魏禧不是为了自己、不是为了一个小家,他将自己的财产、自己毕生的精力,全部投向了动荡社会,为这个社会的变革增添了向前的力量。不仅如此,张良从为韩国报仇出发,最终却拒绝接受王位、反对分封制,全力维护国家的集中统一;魏禧从抵抗清朝出发,拒绝科名爵位的诱惑,最终却为清初文风、士风、学风的转变作出了杰出贡献——他们舍弃“小我”,为中华文明增添了亮色,也在行动中收获了一个完满的自我、一个“大我”。
评价魏禧时,毛泽东焚膏继晷在岳麓山下汲取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。星移斗转,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毛泽东,后来率领苏区军民在赣南大地舍生忘死战斗了六年,六年间,他培育了无数无敌的战士、赞扬了许多无畏的勇士,为众多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颁发了勋章。
而赣南古代,得到毛泽东赞誉的,唯有魏禧一人。
来源:赣南日报
(宁都县融媒体中心供稿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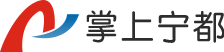



请输入验证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