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我的老师邹卿云
谢直云
1964年,读宁都中学高中时,我的语文老师是邹卿云。
老师五十岁上下,个子不高,上课手拿一本语文课本,看书时戴一副老花眼镜,看同学时眼睛努力地往上翻。不看书时,他把眼镜摘下随手放在讲台上,双目炯炯有神。
老师是宁都县梅江镇人,普通话带有明显的宁都口音,讲到得意处,干脆将普通话换成宁都话,使人觉得特亲切、特有趣。譬如,讲到“睥睨”一词,他会说“斜着眼睛看人:侬多哇咯,打瞧眼。”有女同学“扑哧”一笑,大家都笑了起来。
老师是在旧社会读过老学的人,古文底子很厚实。我注意到当时高中语文教师大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,记得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老师叫王历圣,年近六十;教高64级一、二班语文的曾幼彬老师,教三、四班语文的邹卿云老师都已年满五十了。时年四十岁左右的刘欣大老师是宁都中学老师中的才子,常在报刊发表文章,曾在大学教过文艺理论课,也只是被安排担任初中部的语文教师。
老师最擅长的是讲古文,实词、虚词讲得清清楚楚,从没半点含混。有时,讲到十分投入处,还会以手势助说话,在讲台上走动起来。记得高二的时候,老师串讲《廉颇蔺相如传》一文,讲到“臣观大王无意偿惠王城邑,故臣复取璧。大王必欲急臣,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!相如持其璧睨柱,欲以击柱”时,老师在讲台上作击柱状,一脚踏空,险些摔倒,惊出我一身冷汗。
高中时,两周一篇作文练习,课堂内完成,时间为2节课时。老师的作文命题灵活多变,有时联系时事政治,有时联系学校班级课外活动,有时是一幅画,有时题目出一半、另一半自己加上,后一周进行作文讲评,评定优劣,总结得失。记得有一次作文题目为《飞向……》我灵机一动,写了一篇《飞向北京》。这次作文轮到一、二小组详改,三、四小组略改,我是第四小组的人,属略改的范畴。所谓略改,多半是在作文的后面用红笔写一个“阅”字。出乎意料的是老师竟然对我的作文详改并予以肯定,老师当堂讲读了我这篇作文。一个语文从未受到过表扬的我,突如其来的表扬真让我受宠若惊,当时,我既高兴又难过,既得意又害羞,脸颊像天空的调色板,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糅合搅和一起。老师的评语是“感情充沛”,这四个字竟令我一辈子受益:作文、做人都要充满感情,都要有真情实感!老师的教诲不敢一刻有忘。
事后,我才知道,老师的略改其实是通览,发现好的或者差的,不管是哪一组的,都可以“奇文共赏析”。
老师多次教导我们,要写好文章,条件之一就要博览群书、采纳众长,所谓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。
我们曾多次看到老师在新华书店买书。老师是新华书店的常客,手里捏着一元人民币,走进柜台内随意翻看书架上的书。其他人不行,其他人必须老老实实站在柜台外,叫营业员拿书。有人会说,一元钱,微不足道!可那时,一元钱大约是老师一天的工资啊!
受老师的影响,我也喜欢买书,但我拿不出一元钱来。我得在街上摆小人书地摊,小孩子来看书得交1分钱。我就是1分1分地攒积起来,然后捏着,兴冲冲地跑到新华书店买书。如果能遇到老师也去买书,老师就会为我选书,选得更多的便是杨朔、秦牧、刘白羽的散文集,每次能买上一本,即如获至宝。老师常说,开卷有益。我想,我后来的写作能力有所提高,是与多看课外书有关吧。
老师是旧社会过来的人,难免有旧社会的印记。听说老师在民国时期当过梅江镇镇长,因为社会黑暗,仅当了80天就辞职不干了,以后就一直当教书匠,终其一生!
1966年,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老师受到冲击,听说在一次批斗中,腿骨都被打折了。1968年,我与同学们下放去了洛口。后来,听说老师也下放去了大沽。
再见到老师是20世纪70年代初。老师“平了反”,分配到刘坑中学(现四中)教书。而我则是一个乡村的民办教师。师生重逢,百感交集!老师的一条腿真的瘸了。
再后来,国家恢复高考制度,我上了大学。又再后来,1983年,我从赣州调回宁都工作。一次,我在新华书店门口遇到了老师,他买书的习惯还是改不了。他问我有没有写作了,我说没有。他对我说:写作与当不当官没关系,与爱好有关系、与坚持有关系。那天,老师跟我说了很多,我一直陪同老师回到家。老师住在建国街的一条小巷里,房子不大,摆设普通,但干净、整洁,就像他的人品一样。
由于工作忙,此后再也没有见到老师了。但老师永远在我心里,永远是我敬爱的老师。
哦,忘了说,我是宁都中学高64(3)班的学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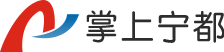



请输入验证码